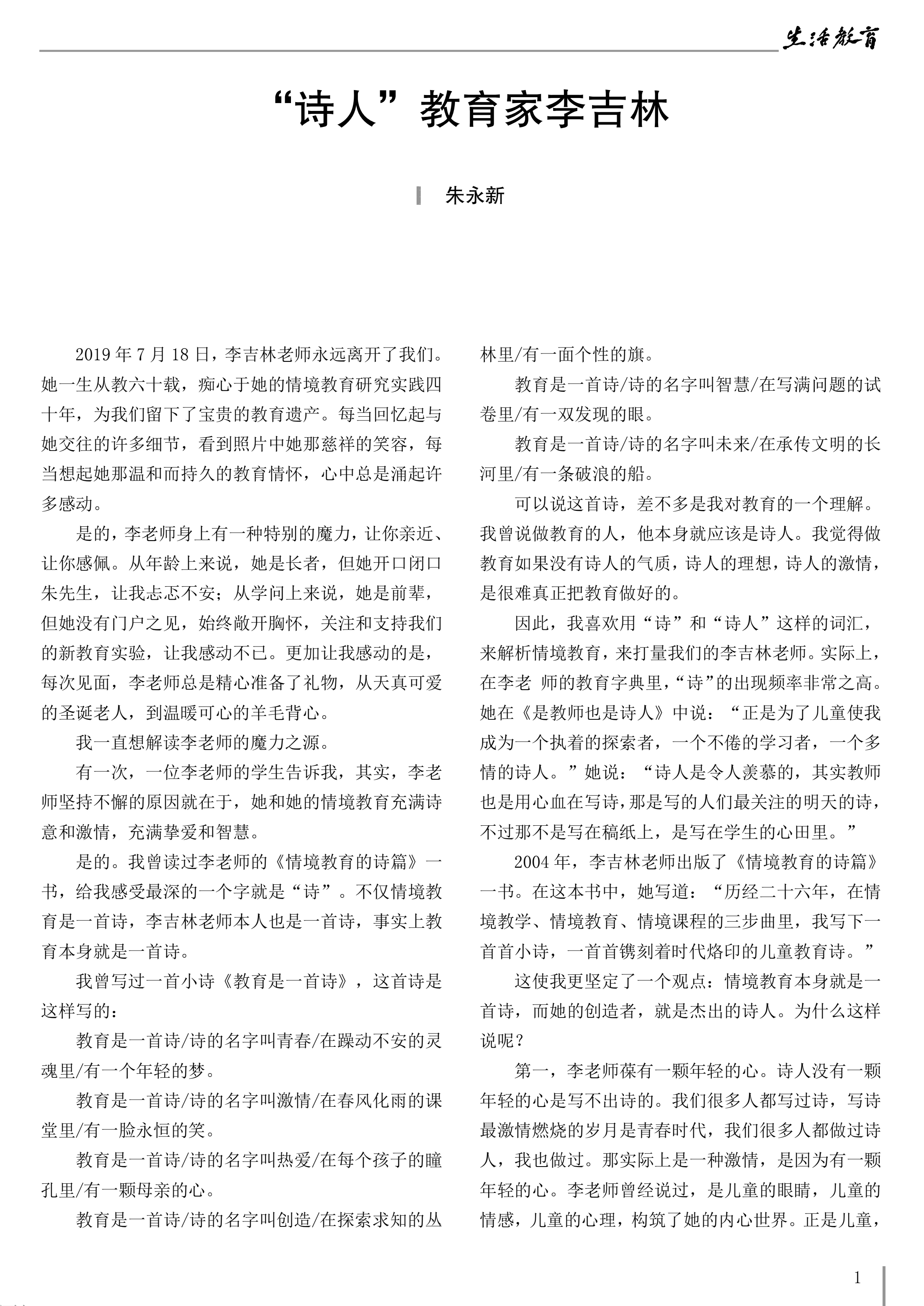“诗人”教育家李吉林
朱永新
发表于《生活教育》2025年10月实践版
2019年7月18日,李吉林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她一生从教六十载,痴心于她的情境教育研究实践四十年,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教育遗产。每当回忆起与她交往的许多细节,看到照片中她那慈祥的笑容,每当想起她那温和而持久的教育情怀,心中总是涌起许多感动。
是的,李老师身上有一种特别的魔力,让你亲近、让你感佩。从年龄上来说,她是长者,但她开口闭口朱先生,让我忐忑不安;从学问上来说,她是前辈,但她没有门户之见,始终敞开胸怀,关注和支持我们的新教育实验,让我感动不已。更加让我感动的是,每次见面,李老师总是精心准备了礼物,从天真可爱的圣诞老人,到温暖可心的羊毛背心。
我一直想解读李老师的魔力之源。
有一次,一位李老师的学生告诉我,其实,李老师坚持不懈的原因就在于,她和她的情境教育充满诗意和激情,充满挚爱和智慧。
是的。我曾读过李老师的《情境教育的诗篇》一书,给我感受最深的一个字就是“诗”。不仅情境教育是一首诗,李吉林老师本人也是一首诗,事实上教育本身就是一首诗。
我曾写过一首小诗《教育是一首诗》,这首诗是这样写的:
教育是一首诗/诗的名字叫青春/在躁动不安的灵魂里/有一个年轻的梦。
教育是一首诗/诗的名字叫激情/在春风化雨的课堂里/有一脸永恒的笑。
教育是一首诗/诗的名字叫热爱/在每个孩子的瞳孔里/有一颗母亲的心。
教育是一首诗/诗的名字叫创造/在探索求知的丛林里/有一面个性的旗。
教育是一首诗/诗的名字叫智慧/在写满问题的试卷里/有一双发现的眼。
教育是一首诗/诗的名字叫未来/在承传文明的长河里/有一条破浪的船。
可以说这首诗,差不多是我对教育的一个理解。我曾说做教育的人,他本身就应该是诗人。我觉得做教育如果没有诗人的气质,诗人的理想,诗人的激情,是很难真正把教育做好的。
因此,我喜欢用“诗”和“诗人”这样的词汇,来解析情境教育,来打量我们的李吉林老师。实际上,在李老师的教育字典里,“诗”的出现频率非常之高。她在《是教师也是诗人》中说:“正是为了儿童使我成为一个执着的探索者,一个不倦的学习者,一个多情的诗人。”她说:“诗人是令人羡慕的,其实教师也是用心血在写诗,那是写的人们最关注的明天的诗,不过那不是写在稿纸上,是写在学生的心田里。”
2004年,李吉林老师出版了《情境教育的诗篇》一书。在这本书中,她写道:“历经二十六年,在情境教学、情境教育、情境课程的三步曲里,我写下一首首小诗,一首首镌刻着时代烙印的儿童教育诗。”
这使我更坚定了一个观点:情境教育本身就是一首诗,而她的创造者,就是杰出的诗人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
第一,李老师葆有一颗年轻的心。诗人没有一颗年轻的心是写不出诗的。我们很多人都写过诗,写诗最激情燃烧的岁月是青春时代,我们很多人都做过诗人,我也做过。那实际上是一种激情,是因为有一颗年轻的心。李老师曾经说过,是儿童的眼睛,儿童的情感,儿童的心理,构筑了她的内心世界。正是儿童,
是童心,给了她智慧。在她70多岁的时候,李老师还对我说,她爱儿童,一辈子爱。如今她已不是儿童,但喜似儿童。“我只不过是个长大的儿童。我多么喜欢自己永远像儿童!”这是一种年轻的心态。特级教师于永正先生曾说要蹲下身子来看孩子,和孩子交流。我认为只要拥有一颗儿童的心,根本不需要去选择和儿童交往的方法,因为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儿童。因此真正的教育家,他肯定拥有一颗童心,拥有一颗无瑕的、天真的、灵动的童心,我认为这是教育的最高境界。
李老师年轻的心还表现在她是一个永远的学生。作为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,全国有那么多的大专家看中她,愿意和她交往,甚至愿意拜她为师,这是为什么呢?我觉得首先就是李老师对别人很尊重,首先她把自己作为一个学生。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末,我在苏州担任分管教育的副市长,一直想挖李老师到苏州来工作,跟她专门谈过把情境教育研究所搬到苏州。李老师当时就说:“我很乐意来向你学习。”虽然因为种种原因,主要是李老师对家乡的留恋,“挖人”没有成功,但李老师的谦逊好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后来在各种场合遇到,李老师也不止一次地说:“如果年轻一些,我就做你的学生去了。”虽然她早已经是一位功成名就的教育家,担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等学术性团体的领导职务,但她还是把自己看成一个学生。不止是我,包括我见到的很多学者,比如朱小蔓老师、顾明远老师,都一致认为李老师非常谦恭,非常尊重有学问的人,非常善于学习,随时把自己看成学生。
正是她这样虚怀若谷的态度,在她身边才能凝聚一大批教育教学研究人员,一大批优秀教师共同来构建情境教育的巍巍大厦。成尚荣、叶水涛、李庆明、冯卫东等一批知名学者,曾经都是情境教育研究的中坚力量。事实上,不仅仅是情境教育,包括我们做的“新教育实验”,包括所有的教育研究,如果没有一批人去为之奋斗,那就不可能做成。现在这个时代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做不成事的。
第二,李老师始终燃烧着激情。做诗人是要有激情的,没有激情写不出诗,没有冲动做不成诗人。郭沫若先生写诗的时候,趴在地上拥抱着泥土的芳香,他必须要有这样的激情,做教育也是如此。我始终认为做教育的人没有激情是做不成的,他最多只能去做学者。著名学者朱小蔓对李老师曾有过评价,说李老师的情境教育追求儿童认知和情感的协调发展,为人的情感发展提供了一个优化的时空。朱小蔓是研究情感教育的。确如朱小蔓所说,情境教育的一个很大特色是:抓住了人类情感这个非常重要的要素。
李老师提出以思为核心,以美为突破口,以情为纽带,以儿童活动为途径,以周围世界为源泉。实际上“情”是一个纽带,情境教育可以把“情境”说成一个概念,也可以把“情”和“境”分成两个概念。
如果从一个概念来说它更多的是一个空间的概念,是一个场景的概念。如果作为两个概念,它本身就是情感和场景的结合。在某种意义上,李老师的情境教育中,情感的要素要大于场景的要素。很多人片面地认为它就是创造一个情景,提供一个时空。我说并不然,更重要的是它的情感要素。教育若缺少情是做不成的。清代戴震曾经讲过一段话,“理也者,情之不爽失也。”没有情感的融入,再好的道理也没有办法让孩子们真正接受。
李老师自己也认为,她就是一团扑不灭的火。改革开放以后,她本来教中高年级的课,后来主动要从一年级教起,为什么这样做?她说:“改革绝对是需要热情,需要主动,需要一股子劲的。”我曾经看到一个网友写的故事,特别感动。她说,2009年的8月22号,他们参加一个学术活动,原日程是看李老师的录像课,但李老师没有让大家看录像,而是亲自来讲。原定讲40分钟,但李老师从3点半一直讲到4点50,讲了整整80分钟,讲到忘情的地方离开了话筒,到黑板上演示她的授课过程。网友说:“这位老人,看上去哪像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,分明就是一位精力旺盛的学者。”为了给大家上好情境教育的示范课,李老师在课堂里给大家哼起了自编的“萤火虫”儿歌,给他们画起了大海,给他们剪起了白帆,给他们折起了纸船。下面的年青教师都很惊讶于李老师的才思敏捷和激情四射。的确,没有这股热情和干劲是做不成教育事业的。
第三,李老师怀有深刻的教育的爱。诗人自然也是有着爱的情怀的。李老师自己曾经也讲过:“正是出于对儿童的爱,使我不怕吃苦,不怕麻烦,意志使我体验到作为人的一种力量。我觉得意志会使人的情感持续、稳定、强化。心理学中写情感和意志是人的两大品质。其实在人的内心世界里两者却难以一分为二,它是互动的,是相互影响的。”因为只有强烈的情感,才会有持续的坚持的力量。
面对应试教育的现实,李老师忧心忡忡,她曾在给我的信中说:“中国教育的问题积聚不少。我总想着儿童、少年、青年的成长:他们的内心有祖国,有他人吗?有愿为祖国效力的志向吗?他们追求崇高,鄙视低俗吗?他们的灵气、潜在的智慧是得到开发,还是被泯灭了?他们的体质和意志比得过日本的青少年吗?”
对教育的忧患意识,是教育家们从来都拥有的,而这些都源于对教育、对未来的深刻的爱。正如有人曾经说过的那样,我看透了这个世界,但是我依然热爱它。所以,在李老师的每一篇文章里面,在她的字里行间,我们都可以读到她对教育的爱。我相信,她的周边之所以能够凝聚那样一批热爱教育的人,也都源于他们对教育的爱。没有他们对教育共同的挚爱,情境教育也很难走到今天。
第四,李老师有创造的智慧。诗人的天性叫创造。从外语情景教学的启示一直到中国古代的意境说,李老师并不是把别人的东西拿来直接翻用,而是在进行一种阐释和创造,并且不断地发展。她从低年级的情景教学,到情境教学实验的研究,再到情境教育理论的构建,包括到最近的情境课程的开发,使情境教育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。这充分反映了李老师善于创造,善于吸收各种知识,包括把新课程的很多理念都在情境课程的作了很大程度上的综合,用自己的情境教育的话语来阐释她对课程的理解,我觉得这是相当可贵的。一个普通的小学老师,她的知识领域,她的学科领域总会受到很大的限制,但是她能不断地学习,就是这样一种精神,这样一种善于创造的激情和智慧非常值得我们学习。
特别让我感动感佩感激的是,李吉林老师在进行情境教育研究的同时,还经常关注和支持我们所开展的“新教育实验”。当她听说“新教育实验”在全国发展很快的消息时,感到非常高兴,并且多次表示欣慰和赞赏,认为新教育切中了当代中国教育的时弊。她还多次鼓励我们继续鼓起勇气,去开拓中国素质教育的一条新路。对于李老师的鼓励,我们新教育人心存感激。李老师还主动表示愿意为新教育做一些她能够做的事情。事实上,李老师真的兑现承诺,与新教育研究院的同事们合作主编了一套新教育的儿童读本。
2010年7月,新教育年会在河北石家庄桥西区召开。本来李老师已作好前来参加会议的准备,并且要在会议上做主题讲演,但因为临时有重要任务而没能成行。但是,令人感动的是,她专门录制了视频演讲托人带到会上。她在视频中说:
“新教育”的盛会我非常想来参加,且已作好一切准备,连发言稿也写好了。但因接到突击任务,不能如愿到会,很遗憾,并向各位致歉!
首先让我热烈祝贺“新教育”第十次年会的隆重召开,今天会场上肯定是济济一堂,因为朱永新主席举起的“新教育”学派的旗帜,吸引了众多的专家、学者和老师,现在已经有了800多所学校加入“新教育实验”,在全国21个省区建成28个实验区。这样的数字真是令人惊喜!由此也足见“新教育”感召力之大!
我思量着:原因何在?
首先是“新教育”的领路人朱永新先生他的宽厚的学识,他的超人的教育智慧,他的对人的亲和与挚爱,他的非同一般的对教育追求的诗一般的境界。朱永新先生作为身处高位的官员对教育仍怀有如此激情,甚至是痴情,且如此深沉而质朴,实为难能可贵,不能不令人感动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朱永新先生的人格魅力衍生了“新教育”的魅力。
有魅力必有追随者,这是必然的。
因此朱永新先生和他的“新教育”足以吸引教育界许多精英、教育家、名师、名校长,连同广大的一线老师,诸如我们熟悉的李镇西先生、李庆明先生、许新海先生,都云集到他的旗下。他们三位并已师从朱永新先生,我羡慕不已,我只能在“窗外”聆听先生的声音。
只是从朱永新论著、诗文中,领略他的壮丽的“教育诗”。对于“新教育”我知之甚少,今天只能将自己一点感悟向朱永新先生和各位汇报。
朱永新先生在“新教育”中从教育的终极目标提出的让老师和学生享受“幸福完整的教育”,引起我极大的共鸣,唤起我对教育更多的美好的憧憬,深感“完整幸福的教育”是顺应人性的,是对教育本质的一种高度概括,因此它是发人深思的。是的,教育本应该是完整的,也只有“完整”的才有“幸福”可言。但是多少年来,教育常常是片面的。我们并不陌生的在现实中仍然存在着的深恶痛绝的“应试教育”。正是破坏了教育的完整,因而导致了教育者的无奈,受教育的痛苦,甚至被扼杀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“新教育”鲜明地提出的“完整幸福”是切中当代教育的时弊。事实已经暴露得很充分,教育的不完整酿造了受教育者的不幸和悲剧,正是教育的不完整,成为国家一直想推行的素质教育的极大障碍。因此,我禁不住要鼓呼、赞美“新教育”,它是解放学生、解放老师的教育,是真正的“新教育”。
“完整幸福”的教育更允许人们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,在不同层次上去追寻“新教育”诗化的梦,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和理解到达“新教育”的不同制高点,因此“新教育”为它的实验者营造了一个宽松的、自由度极大的教育空间。简单地说,“新教育”对教师来说,是大家都能参与,大家都有希望,大家都可以不同程度地享受教育的快乐与幸福,因为朱永新先生追寻的是属于大众的“新教育”。
这又使我很自然地联系到“新教育”的“六大行动”之一的“理想课堂”。“理想课堂”是一个开放的课堂,是一个倡导老师不断地琢磨、不断地探究的课堂,是一个鼓励教师不断去创造的崭新的课堂,课堂本来就是“教无定法”。作为新教育的实验者,在“理想课堂”的召唤下,在实验学校、在实验区教师中一定会就“理想课堂”进行反思、砌磋、碰撞、争辩、实验,于是,教育的创新就发生了。各种风格、各种教法、不拘一格,具有极大的包容性;名师也好,教学新手也行,都有了用武之地。“理想课堂”让五彩纷呈的花朵绽放在实验区、实验学校的校园里。
为了营造“理想课堂”,作为实验者一定会与“书香校园”“共写随笔”“聆听窗外声音”“数码社区”的相关“行动”联系起来,互动互补。这就促使教师从教育的整体性、生成性去体悟“完整幸福教育”的思想的精髓,从而渐入教育理想的高境界,由此必然唤醒“教师和学生的潜能”,“与崇高对话”,不断地激发教师与学生不断向上的内驱力,促使老师在培育学生的过程中造就自我,与学生,而且首先是学生,共享教育的幸福。这种教育的高境界对时下一些教师迫于种种压力,一心为自己怎样成名师、怎样成教育家而忧心忡忡的心理状态,也是一种解脱,对调整自我奋斗航程,起到敦促与导引的作用。
“新教育”的实验与研究,是具有深远的普遍意义,从实验与研究的进程看,无论理论框架的构建还是实验的成效都已获得累累的硕果,令人欣喜。
作为参与课题的结题者,当然是举手表示“通过”。
向朱永新主席学习、向“新教育”的实验的专家、老师们学习。
祝新教育的队伍不断壮大,不断地走向新的辉煌。
李吉林
2010.7.8
会场里上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新教育实验教师们,通过视频感受到了李老师的教育激情,以及对新教育实验所寄予的厚望,令大家非常感动。
应该说,情境教育和新教育实验,在教育界是两个不同的教育流派,但是,李吉林老师完全没有“门庭之见”。李老师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这样说:“应试教育这座大山似难推倒,也没有找准突破口花大气力去推。其实只要集全国之力,从上到下,从学校到社会(包括媒体)协力推,那是一定可以推倒的。推倒的目的是为了青少年的成长,为了民族的兴旺。”在她心里,只要对中国教育有好处,对中国的孩子和老师们有益处,她都会无条件地支持。我觉得,这就是真正的教育家胸怀和境界。
诗人是不老的。作为诗人的李吉林老师,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个真正的“学童”。
(作者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、苏州大学新教育研究院教授)